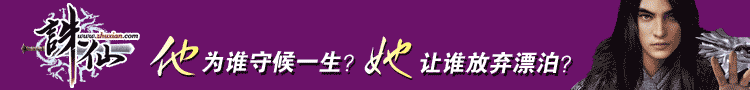
|
|
|
|
曹乃谦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内地出版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4月26日 10:53 新京报
马悦然说“曹乃谦和李锐、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图片来源:曹乃谦blog) 曹乃谦(blog)的名字在国内一直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因为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说过,“曹乃谦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他的文字。 今日,本届全国书市上,曹乃谦写于10年前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简体中文版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这本书是马悦然最推崇的一部作品,被台湾誉为“沈从文、汪曾祺继承者”的山西警察曹乃谦再一次进入了媒体的视野。此外,曹乃谦另一本中篇小说合集《佛的孤独》也将于下月与读者见面。 对于写作,曹乃谦说过:“细节、语言搞好了,才能把读者灌醉,细节是下酒菜,语言是好酒,缺一不可”。 结构 多篇小说“组合家具” 新京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29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汇成一个长篇小说,整体构思巧妙。我发现在《锅扣大爷》一篇的结尾锅扣大爷只吐出一句“把我埋进三寡妇的坟”。而在《三寡妇》一篇中却只字未提“锅扣大爷”,有伏笔,也有留白,是为了让小说更意味深长? 曹乃谦:实际上,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有意把他当一个长篇小说写,而且我有意让这些人物交叉,场景也重复,发表时也是零散发的,我意思是,这本书的篇章都是组合柜,最后一摆,就是完整的一套家具。 新京报:小说里所叙述的事多半发生在1973年和1974年。这两年中国还处在“文革”晚期,但你笔下的温家窑似乎和“文革”的集体记忆并不紧密,那些底层大众的境遇甚至可以被读者想象在任何时间背景下,这是有意为之? 曹乃谦:我就是故意虚化时间。鸡子、狗子都能有解决食欲性欲的问题,人为什么就不应该呢。有人问我,为什么书写出来十年后,你才出这本书?我发现,现在人都说“以人为本”,都关注底层的人了,我想我这本小说现在受到关注,也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虽然那是发生在30年前的故事,但今天依然有人买不起房,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时代在进步,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小说受西方世界关注是因为写出了某些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端。 曹乃谦:那是他们的想法。我没那个意思,虽然我是个警察,可我喜欢坐在农家的大土炕上吃农家的大烩菜,我整个儿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 天不下雨,我就替农民着急,下得多了,我也替他们着急。 我的小说在关心关注我的父老乡亲。马悦然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我说“悦然懂我,悦然懂我”。 情节 想象中的真实故事 新京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故事发生在“温家窑”,这个在大同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故事里头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可怜的光棍儿。除了渴望吃饱以外,他们都渴望跟女人睡觉。有意思的是,口里装满了脏话的光棍把“睡觉”说成“做那个啥”。两个贫穷的光棍儿买不起女人,竟然紧紧搂抱,没完没了地亲嘴…… 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吗? 曹乃谦:“温家窑”是我想象的,真正的村子原型叫北温窑,但整个雁北地区,人们的生活都是那样。我给你讲一件真事。1974年,我被派到北温窑村给插队知青带队。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跟我说他刚才吃过饼干了。原来是知青去供销社花了很少的钱买了饼干末,他用舌头舔着吃了一口。你想想,大队最大权力者的儿子居然是这样。 实际上,我并没有把很多的悲伤的事情都写出来。 新京报:会不会担心有的读者以猎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真实的故事? 曹乃谦:我什么都不担心,他怎么看,是他的事。有的人看长篇小说,一看是讲爱情的,哗哗哗哗翻过去,就看“做那个啥”了,这跟我没关系,我不是为他们写的,我为喜欢我的读者写,我为我笔下的主人公写。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很多女性形象让人久久不能忘记,比如在大喜的日子里,给玉茭娶鬼妻放声大哭的玉茭妈,为什么你笔下的女性那样伟大? 曹乃谦:在我的笔下,女性的结局都是悲剧,但我把她们写得那么美好,她们又是那么的胸怀博大。我把女性全部神化了,犯罪的女性也是美好的罪犯。我的小说不会让任何一个女子说出“我爱你”,她只会说“要不今天,我就把我给你了吧。”我已经写出了比说那三个字更美好的意境。 我再给你讲个真事。有一年,我爸爸当公社书记,我放假去村里看他,我们住的一个院子里就有这么一家人。一个女人嫁给了两个男人,一月份归一个男人,二月份送回来归另一个男人,就这样过呢。后来我把它写进书中《亲家》一篇。 语言 改成普通话就不是我了 新京报:听说你小时候老跟着个放羊倌听他唱山曲,所以你的小说里语言充满了山曲的味道。 曹乃谦:小时候,农村姥姥家村里有个叫疤存金的放羊倌,他会唱很多山曲。我常哄姥姥说到野地背书,瞒着家里人跟他去放羊。他唱的时候老痴痴地盯着山下的村庄,唱:“对坝坝圪梁山那是个谁,那是个要命鬼干妹妹。崖头上的杨树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数干妹妹好。”唱完,他坐在那里半天不作声,随手摸住身边的土坷拉往坡梁下狠狠地扔。过了四年我听说他上吊死了。《天日》一篇里的羊娃原型就是疤存金。 我在小说里,大量引用了“山曲儿”、“麻烦调”、“苦零丁”、“伤心调”、“要饭调”、“挖莜面”等,只有这些民歌才能表达出人们对食欲性欲得不到应有满足时的渴望和寻求。 新京报:你小说中对话里所运用的粗话粗得吓人。诸如“狗日的”等言谈放在那些人物身上却让人恰如其分,出版时有没有什么争议? 曹乃谦:我就只会这一种语言。其实我写的时候没想过用个什么语言写,我原来就不知道小说语言还有什么规定。 我就用我自己的口语写出来,我的小说就是我的口语,而且当地人也这么说。所以好多编辑要把我的语言改得规范的时候,我很气愤,弄得文绉绉的,我来不了,我说:“你改得不像我说的话了。”有人就问,你不是说,你喜欢很多外国小说吗,你写作是不是在模仿他们?我喜欢斯坦贝克、海明威的小说,但我写的时候,就用我自己的语言写。 新京报:你小说中的很多方言,会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吗? 曹乃谦:以前我也不注意,现在有南方读者说不理解,我说,你看不懂,还有前后语境可以猜猜。有的编辑还建议我把语言换成标准普通话,我说,那就不是曹乃谦了。 新京报:马悦然说过“在我看来,曹乃谦也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提高了你在国内文坛的知名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曹乃谦: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曹雪萍) (编辑 小题)
【发表评论】
|
|||||||
